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声音描写
时间:2021年05月12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文章聚焦丁玲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声音描写为分析视点,观照作品内部叙事层面的他者之声、外部社会现实之声与作家的话外之音,感受丁玲对底层人民、女性命运等社会他者的关怀。丁玲在热情高涨的氛围中,以革命者应有的理性精神与高度责任感,审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外部现实之声在影响创作的同时,也与作家内部的心声相互碰撞,产生混响的艺术效果和张力。
关键词:延安时期;革命声音;丁玲;女性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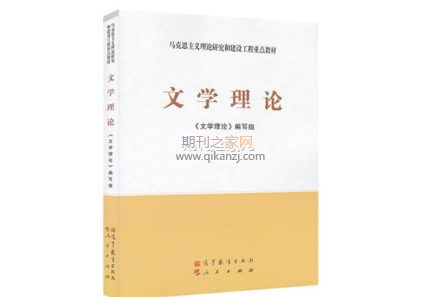
我们正处于高度依赖视觉的“读图时代”,手机、电视、电脑等电子工具,加剧了人类对眼睛的使用,这无形中挤压了视觉之外的其他感觉方式。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主题为“对倾听的思考:人文科学的听觉转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影响国内的文学研究由“视觉”转向“听觉”描写,有学者提出对于经典作品要进行“重听”,“它当然也是一种‘重读’,但这次是以经典中的听觉叙事为阅读重点”。[1]本文聚焦丁玲延安时期前后的作品,观照延安时期的外部现实之声、作品内部的叙事之声以及作家的话外之音,以声音描写为分析视点,重新解读经典作家作品。
丁玲初入文坛时的作品,受到五四启蒙精神的指引,旨在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寻求个人的解放,书写对象也多以女性个体为主。而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丁玲在上海接触左翼思潮,这也为当时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丁玲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她的作品开始向革命立场转变,出现了“革命+恋爱的公式”[2](P340),也出现了对于革命背景声音的描写。
随着丁玲本人对左翼文学理解的深入,描写的对象也从个体延伸至社会中的底层人民,《水》是丁玲在这一阶段具有转折性质的作品,不仅题材开始触及底层,更别具新意地调动听觉描写,这在同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常见。丁玲来到延安后,有感于丰富激情的革命声音,不仅弥补了较城市相对贫瘠的视觉文化,而且强大的革命声音也激发了丁玲对于伟大革命事业的想象。而在热情高涨的各种声音中,丁玲以理性精神和敏锐眼光,审视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女性以及被忽视的社会问题发声,这也彰显了一名革命者的高度责任感。此时的延安,出现了外部现实之声与内部文学之声的混响现象,这说明延安时期的声音对于革命理想与个体理性思考的巨大影响。
一、到延安前:革命之声与底层书写
在丁玲早期的创作中,《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具有代表性。“她早期的作品便是‘在黑暗中’发出的苦闷的绝叫,也是对自己苦闷、寂寞的灵魂的一种自我救赎。”[3](P144)丁玲毫不掩饰地叙写女性在身体与欲望层面的正常诉求与主体声音表达,用启蒙下的个人觉醒冲破封建的精神桎梏。但从三部小说的结局我们看到,丁玲陷入了苦闷之中。梦珂最终屈从于男权、消费社会之中,成为都市欲望的消费品。莎菲则身患肺病决计南下,对爱情失望后看淡生死。而阿毛则是香消玉殒于男权社会和封建礼教。这也让丁玲再一次思考个体觉醒后应该走向何方?小说中死亡的命运或许是她思索无果的无奈之举,可见此时的丁玲陷入启蒙者迷茫的精神困境中。
20世纪20年代末期,革命文学运动和左翼思潮发展方兴未艾,这也让处于精神困顿之中的丁玲有了新的方向。在当时的文坛,启蒙落潮后新的呼声开始出现,普罗文学旨在文学与革命紧密结合。丁玲此时的创作也呈现个人向集体、恋爱向革命立场的转变,例如《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韦护》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这是丁玲小说由启蒙到革命转变的早期创作,除了革命+恋爱的题材选择外,丁玲也开始尝试在小说中用声音的描写来反衬革命这一大背景。在这类小说中,革命与爱情之间往往是矛盾冲撞的,一种是革命改造爱情,一种是为了革命而牺牲爱情,而丁玲的创作往往采取后一种路径。
丁玲初入文坛时,是为了女性婚恋自由而发声,她对于恋爱自然是投入了更多的情感,但从结局来看,不论是韦护和丽嘉还是玛丽与望微,丁玲都选择将结局导向为了革命而牺牲爱情,可见她革命的声音多么强烈。丁玲1930年创作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结尾处,当玛丽离开后,望微投入演讲与革命的队伍中,“在马路那边,蓦的噼噼啪啪响起巨大的爆竹声,只听见各种的口号便如雷的响应着”[4](P336)。
这是小说中丁玲对于革命场面少有的声音描摹,望微放弃了小我的爱情,投身大我的革命事业中,同时这如雷的、集体的声音让望微和在场的革命者都“有点兴奋,压抑不住的,仿佛看到那爆炸的火山,烈焰腾腾烧毁这都市”[4](P336)。丁玲在结尾利用声响描写来表现革命是别有深意的,首先从叙事层面看,爆竹声、口号声这些都是无形的事物,但在声音的笼罩下,小说中的人物仿佛看到爆炸的火山,这又是有形的,这一手法正如傅修延在《听觉叙事初探》中提到的“听声类形”[1],将听到的声音类比为视觉形象,将无形化为有形,这不仅使得声音更为形象,也激发了读者的想象。
其次,这一情节的设置也让我们感受声音背后所附着的政治、文化意识对听觉主体所造成的强大的心理震撼,“声音技术以其独特而有效的编码逻辑,显示了对自我意义的侵犯、渗透、改造和创生的能力”[5],也即由意识形态所包围的声音空间,甚至会对主体产生强大的导向作用。随着左翼思想的不断深入,丁玲将书写的笔触真正触及底层人民,丁玲的《水》是以1930年波及17个省市的大水灾为背景,描摹了底层群众抗击水灾的场面并刻画了农民灾后自发奋起反抗地主的群像。
在《水》中丁玲大范围地运用了听觉叙事,代替了在黑暗中较为失效的视觉描写,《水》的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但其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无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6《]水》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却走出了模式化、公式化的创作路径,也迈出了丁玲表现自我心理的小说定式,开始关注社会他者的底层书写,她在小说中大规模地使用声音描写来调动读者的听觉想象。在《水》中,丁玲充分调动了非视觉化的感官描写,激发读者对于在暗夜中农民抗击水灾的阅读想象。作家的声音描写,烘托出灾难面前人内心的惶恐与不安。
“远远似乎有狗叫。风在送一些使人不安的声音,不过是一些不确定的声音,或许就是风自己走过丛密的树梢吧。”[4](P400)在视觉几乎失灵的黑夜,水的吼叫、风的呼啸都往往会使人心神不宁。“风远远的吹来,一直往屋子里飞,带来了潮湿的泥土气,又带来一些听不清,却实在有点嘈杂的人语声,远远的,模模糊糊一些男人们的说话”[4](P407),人的私语与嘈杂暗示出此时人内心的慌乱不安,远处模糊的男人的说话也说明前方抗击水灾的紧张场面,不同于视觉给人带来直接性的震撼,听觉的描写似乎是循序渐进却又深入人心。
之后一阵急促的锣声打破了恐惧且平缓的节奏,“虽说是远远的传来,声音并不闹耳,可是听得出那是在惶急之中乱敲着的,在静夜里,风把它四散飘去,每一槌都重重的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4](P409)。锣声的登场表明大水的来临,这吃人的洪水已经迫在眉睫,孩子的哭声、妇人的叫喊声也随之而起,急促的锣声加快了小说叙事的节奏,底层的百姓即将开始抗击水灾。在大水侵袭之后,剩下的是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抗击水灾的过程中,水势的平缓与凶猛、人心的惶恐与不安、抗洪的挣扎与勇敢均在声音的此起彼伏下推进展开,将水灾的无情与底层人民齐心协力的抗灾群像,有张力且无缝地衔接起来。
日本学者中岛碧说:“这与她以往的文学——自我表白型的心理小说——相比较,不能不说在题材上、方法上都是极大的变化。”[7](P538)去延安之前,丁玲就已经开始接触左翼思潮与革命文学,并自觉地转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启蒙走向革命,由个人自我下沉至底层,这也说明丁玲逐步转向革命的立场。此时丁玲的创作中就已经初现其对声音、听觉的关注与运用。借用声音描写对演讲、革命场面进行描摹,反衬底层百姓在压迫下的艰难处境以及在抗灾中强大的团结力量。声音描写一方面体现在叙事层面,唤醒读者的听觉想象,另一方面折射在政治、思想、文化层面,说明革命对于激发个体的家国热情、反抗崛起的重要作用,而后者在丁玲进入延安后,有了更加明显的呈现。
二、初入延安:激情的革命交响
经历了上海时期的向左转向后,丁玲已然成了一名有影响力且较为成熟的左翼作家。此时丁玲的文学立场开始从个人转向集体、由启蒙迈向革命,这从《韦护》《田家冲》《水》等作品中可窥见一二。
在此之后,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囚禁于南京。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延安革命中心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初获人身自由并来到革命中心的丁玲,有感于延安丰富的革命声音,演讲、朗诵、合唱、平剧等组成了激情的交响,这也激发她对于革命的想象,她开始用文学之声热情地歌颂革命,并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新的信念》等一系列作品。
这些作品中涉及性压迫、性暴力等女性问题,彰显了丁玲对女性命运惯有的思考和关怀,同时在作品中也展现出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等尖锐的社会问题。丁玲初入延安时期的书写,与延安的革命声音是分不开的,激昂澎湃的声音对于调动主体的革命积极性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来到延安后,丁玲感受到延安相对荒芜的自然风光,不同于夜上海的灯火通明、声光色影,现代都市空间给人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
例如,在丁玲早期的创作《梦珂》中,梦珂来到生活在都市的姑母家,感受到完全不同于乡下的丰富的视觉体验,看电影和话剧,都市通明的灯光与圆月剧社耀眼的聚光灯,令梦珂感到新奇又不适。而在延安,视觉体验上的相对暗淡,并没有阻碍延安文艺的发展,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详细讲述了她来到延安后所感受、观察到的一切:“说苏区没有文艺,那是非常错误的!”[8](P18)延安的文学作品是深入群众的,具有大众化、普遍化的特点,在文艺上“呈现出活泼、轻快雄壮的特点。
最能作证明的,便是在苏区流行着好似比全中国都丰富的歌曲,采用了江西、福建、四川、陕西……八九省的民间歌谣,放进了适合的新的内容”[8](P19)。可见延安文艺中,歌声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极为活跃的。除了丁玲,其好友陈学昭在1938年来到延安后,对于这样一个歌咏之城印象也极为深刻,她在《延安访问记》中多次提到延安的歌声也使她内心感受到无比的激动和震颤。
在《黄河大合唱》中,激昂的旋律、奋进的歌词,即使是身处当下,也能感受到国难当头,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战的坚定决心,“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不能不激动起你的热血与激情!”[9](P130)而除了歌声以外,在延安还经常举办一系列的演讲活动,“在延安,这是一个奇迹,好像全中国的演说家都集中在边区”[9](P180)。丁玲初入延安也负责组织编排戏剧,她一边创作、一边编排、一边公演,独幕剧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结合当地的民谣锣鼓唢呐,再结合歌舞,总的一个方向,就是贴近大众。
在延安,演讲、合唱、歌声、朗诵、戏剧等文艺活动交织出一曲激情声音的交响。视觉文化的相对缺乏并没有阻碍延安革命声音的蓬勃发展。声音的交响拉近了外部世界与听觉主体间的距离和界限,个体自然地融入其中,燃烧起抗战、革命、奋斗的激情与热血。
同时,这也激发了她对于民族革命的想象,丁玲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东村事件》与《新的信念》,是值得关注的。二者都是将叙事的目光聚焦于女性身上,也同样反映了女性所遭受的性压迫与性暴力问题,但同时故事的深层意蕴也不限于此,而是将矛头直指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这一宏大的现实问题,并折射出谋求民族抗争的创作主题。
在《东村事件》中,七七是一个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用贞操换来了自由的可怜的女性。但悲哀的是,她的失贞并没有换来未婚夫的理解,反而因此遭受拳打脚踢,七七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待。这体现了封建礼教、传统贞操观念对女性的压迫,同时这种仇恨也升至阶级斗争的高度,为了给七七报仇,底层的百姓奋起抗击地主阶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场关乎阶级的矛盾中,七七始终处于沉默的状态,而这与《新的信念》当中的陈老太婆的反应截然不同。
在《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遭受了日军的性暴力,但是她似乎并不掩饰自己作为慰安妇的经历,在叙述那段惨无人道的经历时,她并不遮掩,反而像是宣传,乐此不疲地到处倾诉这段经历,通过她的极具鼓舞性质的声音激起百姓对侵略者的愤怒,最终指向反对外敌入侵,谋求民族解放和统一的主题。初入延安的丁玲,感受到苏区丰富多样的声音文化,这些关乎革命、民族、青春的声音一齐交织出激情昂扬的延安交响,使得身处其中的革命者听后,充满热血与斗志。丁玲融入这一伟大的交响当中,满怀着革命的激情与信心,谋求民族的统一与解放。
三、深入延安后:女性命运关怀与理性革命精神之声
随着丁玲在延安深入生活,她逐步摆脱了新奇感以及随波逐流的热情,以一名革命者应具备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眼光审视着现实中的诸多问题。1942年,在散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敏锐地捕捉到在旁人眼里看似生活滋润的女性背后所遭到的非议以及暴露的婚恋问题。
女性作为他者仍然是受鄙视的,即使是知识分子以及成功出走的娜拉,最后仍然回归家庭与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丁玲小说创作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丁玲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关注到在延安地区被人们忽视的婚恋、男女性别失衡等有关女性自身解放的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当属《在医院中》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我们可以着重观照小说中出现的声音描写,包括叙述者以及其他人物的声音描写等,从中感受作家对于女性他者的关怀以及自身的理性革命精神。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有几种声音描写值得注意。书中的“我”是作为作者的第二个自我,也可以说是一位叙述者,她对所见所闻进行观察和描摹。我所听到的贞贞与现实中的贞贞,是不对等的,存在一种反差,听与被听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除了叙述者、隐含作者的声音描写之外,还有贞贞的、阿桂的、盲众的以及青年们的声音描写,这些声音描写背后体现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性别立场。
小说的前两部分并无贞贞出现,开头是以叙述者“我”来讲述和同伴阿桂一起来到霞村时的场景,“我”所见到的霞村并非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热闹,相反较为冷淡和萧瑟。“但当我们走进村口时,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只是几片枯叶轻轻地被风卷起,飞不多远又坠下来了。”[10](P214)前面环境的铺陈是较为冷清的,但是后面贞贞的事情却是村民口中热议的话题。这一冷一热之间产生了具有反差的艺术张力。随后小说中陆续出现众多的声音描写:院子里“看见没有?”“看见了,我有些怕。”[10](P217)以及青年人口中的“刘大妈的女儿贞贞回来了。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10](P218)。
还有阿桂半遮半掩地讲:“呵!我们女人真作孽呀!”[10](P218)第二天她听到杂货铺的老婆对贞贞的贬低“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10](P219),妇人们对贞贞的议论“她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10](P219),还有杂货铺老板站在男权的道德立场上的发言,“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10](P219)。这种种的人物声音描写造成了一种谜一样喧哗的氛围。众生喧哗的声音下潜伏着不同立场、阶层人对于贞贞的态度。
妇人们以及杂货铺夫妇站在男权社会和封建伦理的贞操观上对贞贞进行道德诋毁。而青年们则站在革命的立场对贞贞这种舍小我的行为进行由衷赞扬。阿桂的形象则少有人注意,其实从小说开头我们不难发现,阿桂起初对待叙述者“我”的态度十分冷漠,但是碰到村民时却极为热情,在百姓眼中阿桂是个亲民的好革命者。阿桂行为的前后不一致也撕开了她虚伪的面纱,而在贞贞的问题上,同为女性的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但这同情是出于真心的吗?
做女人成了作孽的事,这将矛头直指本为受害者的女性主体,女性自身的贬低也让女性解放道路变得道阻且长。这些都是叙述者“我”所听到的贞贞,那么贞贞难道真如盲众所说得那般龌龊不堪吗?恰恰相反,叙述者所听到见到的贞贞是令人欣喜的,“阿桂还没有说完,便听见另外一个声音噗哧一笑:嘻……”[10](P222)
这笑声是那么的俏皮活泼,随后的交谈也是贞贞率先开口,这也是她爽朗性格的一个直接表现。在提及那段不堪的回忆时,贞贞没有一味地宣泄苦痛、贩卖悲伤,而是以一种较为平静地姿态诉说着:“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10](P225)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前后文中感受到贞贞形象的反差,在盲众口中贞贞受尽伦理贞操观的束缚,在革命青年口中贞贞是勇敢且具有奉献精神的。
而在叙述者口中“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10](P226),这也是隐含作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贞贞的评价。丁玲对女性他者的关怀更多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是摆脱了封建礼教和世俗规约的。丁玲另一部小说《在医院中》,也展现女性敏锐的感知力与其对问题的理性思考。陆萍是上海产科学校毕业的一位年轻的女知识分子,从小说开头就叙述她穿着男性的衣服并处处用讨好的腔调。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知识分子放下身段向工农阶级靠拢。
这种自我改造的表现是否得到群众的认可?小说中的一些声音给出了答案。“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10](P236)从老乡的略带鄙夷的声音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出,到延安革命的妇女可能很多时候是背负着生育的重担。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身份并未得到百姓的认同。在延安,妇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冷漠的,从陆萍和看护张医生老婆的对话中即可听出,对于新来的陆萍,张医生的老婆“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10](P237)。
她们并无互帮互助亲如姐妹的意思。最初陆萍在医院中是极受欢迎的,大家都将希望寄托于她身上。但随着深入生活,她发现了医院中的种种陋习:环境的脏乱差,人们没有卫生的意识,医护人员缺乏护理的常识等。但她却依旧在医院中坚持着自我的习性,渐渐地,医院出现了许多异样的声音,大家开始在背地里讨论陆萍,认为她是个怪人。陆萍作为一名带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革命者是不被周遭人理解的,她也成为人群中的他者。
其实丁玲在这部小说中,发出的问题之声并非是孤立的,在《延安访问记》中,陈学昭直言一些办事机构“太不科学,太手工业化”[9](P215),并且在医院中也缺乏准确计时的钟表,设备也相对落后。陆萍此时发出的声音是对现实不合理问题的理性思考,这种被周遭人视为他者的声音看似与革命集体相对立,但“就其本质来说,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11]。
不管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还是《在医院中》,此时期丁玲的作品有力地显示出其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她以革命者的理性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审视和思考现实中的问题。而在小说中的叙述者声音描写,也恰恰折射出作家的话外之音,这类声音与外部的声音相碰撞,产生出混响的艺术效果,延安时期丁玲的声音描写不仅促进作家对于民族解放任重道远的思考,也形成了声音描写对于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无法忽略的作家,她以自身独特的女性体验,敏锐地感知并书写着女性命运在现代社会中的浮沉,“历史的风云变幻、个人命运的传奇性沉浮与创作面貌的变化这三者在她身上纠结得十分紧密,大体上可以说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多棱镜”[3](P141)。在她的作品中始终展现出对女性命运、底层百姓等社会他者的深切思索与关怀。在延安时期,她在丰富激情的革命交响中,关注现实存在的问题,显示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1]傅修延.听觉叙事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2013(2).
[2]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A].茅盾文集(卷20)[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4]张炯.丁玲全集:第3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J].文艺研究,2017(11).
[6]茅盾.女作家丁玲[N].文艺日报,1933-07-15.
作者:赵泽楠
SCI期刊目录
SCI论文
- 2024-04-20怎么查sci期刊是几区
- 2024-04-20作物栽培学英文sci期刊推荐
- 2024-04-20SCI录用后能在网上检索到吗
- 2024-04-20sci论文初审就被拒稿的原因
SSCI论文
- 2024-04-18ssci论文更快接收的技巧
- 2024-03-27SSCI二区论文有什么快速发表的办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 2024-03-16热门推荐87本管理学领域ssci期刊
EI论文
- 2024-04-17电气电力方向2024年的学术会议
- 2024-04-12EI会议发表文章的流程
- 2024-04-12真空、陶瓷、绝缘方面的会议怎么
- 2024-04-11Journal of Electrical Systems
SCOPUS
- 2024-04-15SCOPUS检索的会议怎么找
- 2024-03-23Scopus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属于什么
- 2024-03-14scopus论文着急见刊怎么弄
- 2023-12-25艺术教育论文可以发到scopus吗
翻译润色
- 2023-05-13神经生物学英文文章如何提升英语
- 2023-05-12sci论文润色的意思
- 2023-05-11生物医学sci论文润色有用吗
- 2023-05-09锻造相关中文文章怎么翻译为英文
期刊知识
- 2024-03-21论文发哪些期刊符合评高级职称要
- 2024-02-21论文发国际期刊的五大优势
- 2024-01-13英文、中文期刊傻傻分不清楚?这
- 2023-12-20地质比较好发的期刊
发表指导
- 2024-03-06哪些食品类期刊被ei收录
- 2024-02-29图书资料副研究馆员职称有学术专
- 2024-02-23准备评正高需要什么学术成果
- 2024-02-22论文发英文期刊原始数据包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