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成为我的私敌”:论基尼亚尔的语言思辨
时间:2020年11月27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帕斯卡·基尼亚尔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其著作丰硕且屡获文学大奖。 受家庭影响,基尼亚尔自幼便开始接触语言学,对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对语言问题的思辨构成其作品的重要内容。 基尼亚尔探寻语言的原初,认为语言是后天获得之物,人获得语言意味着获得身份,也意味着失去最初的真实世界和整体性,失去自主权。 作家指出,语言作为纯获得之物的本质决定了它会随时消失,跟讲话者分离。 在这个意义上,基尼亚尔把语言视作“私敌”,用写作这个能够在表述的同时保持沉默的绝妙方式质疑、对抗约定俗成的语言,其作品因而成为沉默文学谱系链上极为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基尼亚尔 语言 私敌 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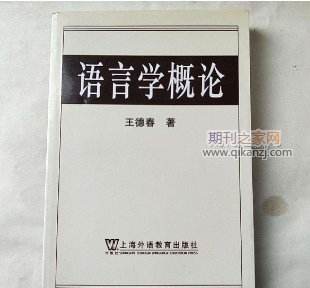
引言
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 1948-)是法国最具实力和创新性的当代作家之一。 自上世纪60年代末出版第一部作品以来,他已有80多部作品问世,被誉为“熔历史想象、文学虚构、艺术审美、哲学思辨为一炉的创造性写作”。 基尼亚尔的创造性写作跨越多个学科,游移在文学体裁的边界,并实现多体裁的融合。 尽管基尼亚尔的作品以杂糅为特征,但总围绕着原初(origine)主题展开。 而作家对原初的探寻在作品中通过一条主线呈现出来,这条主线就是语言(langage)问题,“对语言的忧虑处在帕斯卡·基尼亚尔作品的核心地带。 ”那么,对基尼亚尔来说,语言是什么?
1998年,基尼亚尔出版《秘密生活》(Vie secrète),在这部被称为不朽之作并获法国文化大奖(Prix France Culture)的作品中,作家写到:“当语言尚未以令人讨厌的声波形式在空气中传送时,还不是我的敌人,但自此之后则成了我的私敌。 人们不会心血来潮地把音乐、文学视作生命中的最爱。 如果人们只是想生存下去,话语无非就是一些难以信任的新鲜事物,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
为什么语言悖论地成为做“语言工作”的作家的私敌? 私敌的蕴意是什么? 如何评价基尼亚尔作品中语言和写作的关系? 本文将从基尼亚尔对语言的思辨出发,提出沉默是其文学创作的思考路径之一,以期引发更为深入的对基尼亚尔作品的阅读和探讨。
一、天赋还是获得?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学术界出现一次巨大的转向,即语言转向,语言问题一跃而成为人文科学的研究热点,人们在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对语言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和探讨。 而语言的原初,由于人类最初语言体验记忆的缺失,以及对语言如何出现、何时产生等问题的无从回答,成为语言研究的焦点问题。
关于语言的原初,学界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以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为代表的语言天赋论,认为语言是人的生物属性,人类语言存在普遍语法(grammaire universelle); 与语言天赋论相对立的语言文化论,强调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本质上属于社会行为。
生于二战后且自幼接触语言学、对语言产生浓厚兴趣的基尼亚尔不可避免地受到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语言理论影响,作为文学者,作为最纯粹最古典意义上的“文人”(魏柯玲:99),基尼亚尔对语言和语言原初问题的思考——借用作家自己偏爱的术语,思辨——从未间断,并在作品中反复提及多次论述,他博采众家之长,更看重探求的过程,而不是唯一的答案或确定的知识:“别忘了我不言说确实无疑的东西。 我让我出生的语言在其痕迹上前行,这些痕迹和阅读还有梦混杂在一起。 ”
如果基尼亚尔言说“不确定”,那么,对于语言的原初,他的观点是什么? 认为语言是人固有的普遍能力? 还是相反,认为语言跟写作、艺术一样,是后天获得之物? 基尼亚尔在《小论著》(Petits traités)中不无直接地指出:“语言为万物之源,却非语言之源。 ”他通过“向前回溯的运动”去界定“万物之源之源”。
首先,基尼亚尔把爱神(Eros)定义为张力,认为这种张力没有意识,就像人睡梦中性器官的勃起,人因无意识的性勃起而心生恐慌,从而引发语言出现。 在基尼亚尔看来,语言最初用来命名人内心的恐惧。 在这个意义上,梦是语言原初的重要维度之一。 随后,基尼亚尔指出语言出现跟狩猎有关:“在捕杀猎物的想法中,(语言)已经剥掉猎物的存在(树林,羽毛,獠牙,皮,肉)。 ”也就是说,语言原初是捕食前的准备。 不难看出,基尼亚尔对语言原初的思考带有明显的悖论:狩猎活动表面上一言不发,事实上却是语言行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基尼亚尔眼中,作为万物之源的语言带有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作家还认为,语言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不可抹去的集体特征,属于集体行为,因而有可能引发分裂和恐惧。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起初,人猎杀野兽是为保证自己的存活; 后来,狩猎发展成人残杀人,即对同类的杀害。 基尼亚尔认为,既然人通过模仿捕杀猎物,也通过模仿杀害同类,那么同理,模仿也是文学的原初。 语言的原初带有猎杀体验的痕迹,是触碰已失之物的最佳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对已失之物的唯一复兴。 ”
如果说梦中无意识勃起的性器官、狩猎行为、人人之间的残杀促成话语的生成,那么交流、表达、满足需要就成为语言的主要功能,即通常所说的“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另外,语言对文明的推进也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然而,在基尼亚尔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展现和繁衍生命的肉体是其(生命)唯一的真实面目。 话语并不构成其脸面。 生命的存在并不依赖于语言。 言语只是一种奢侈品,没有它,生命依旧可以继续。 当我们说话时,并非生命的本源在说话……这也就是话语的无用之处,远胜于其危害。 ”(基尼亚尔,2014:54)作家运用各种否定强调语言功能的不在场,并指出,语言不是人的本质。
如果语言不是人的本质,那么如何定义人的本质?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在其《童年与历史》(Enfance et histoire)法语版序言中写道:“人不局限于‘知道’,不局限于‘说’,人既非‘智人’(homo sapiens) 亦非‘语人’(homo loquens), 而是 ‘智语人’(homo sapiens loquendi)。 ”基尼亚尔赞同阿甘本的观点,但同时指出,人的“智语人”特征不明显,因而他选择从人非“智”非“语”的否定性出发,像达尔文、海德格尔、超现实主义者、巴塔耶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那样,重新审视人类中心论,表明人-语言-文化之间的割裂和分离关系,因而“人类的动物本性始终是其作品的内容,包括捕食性反射、在进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一种记忆和本质上的非线性时间等方面。 ”
在确定动物性为人的本质后,基尼亚尔的语言原初观也随之明晰,在他看来,“语言不是我们的反射行为。 ”(Quignard, 1993: 57)语言不是人固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一种能力。 由此,基尼亚尔认为,在跟语言的关系中,人的自主权是缺失的,是不在场的,语言随时有可能跟人产生分离:“语言没有生命。 语言不是活组织。 语言不经历纯粹意义上的增殖或衰退。 它既无再生也无衰落。 ……语言也不是悖论的约定符号的发声系统。 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语言制造符号吗? ……语言不服从‘熵’,不新生,不灭亡。 ”(Quignard, 1990: 149)
基尼亚尔更是进一步指出,语言虽然没有生命,但却拥有无所不在的权力,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 因而,人与语言之间体现出某种服从关系。 也就是说,一方面,生命和语言之间处于分离、割裂的状态; 另一方面,语言对个体施加权力,人变成语言的囚犯,遭受语言的控制。 对于这一点,巴特(Roland Barthes)也曾明确地表示:“我总是不得不选择阳性或阴性,对我而言,中性或复合性是禁止的; 甚至,我还不得不用‘你’或‘您’来标明我与他者的关系:对我而言,情感或社会中断是拒绝的。
因此,经由结构本身,语言指涉某种致命的异化关系。 说话,或者,谈论,不是我们不厌其烦所说的交流,谈论是奴役。 ”基尼亚尔赞同巴特的语言异化论,认为讲话者在自我命名和命名世界的时候,异化就已经出现。
语言不仅对个体施加权力,还具有欺骗性。 在作者看来,“言语就是说谎。 ”(基尼亚尔,2007:45),“我们身上所有的语言,都不是根基,都在被盗用,它是一个骗子。 ”基尼亚尔对语言的效用产生质疑:“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中,最贫瘠的声音是语言声音。 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中,最有害的是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声音让人以为是它们赋予世界意义。 ”(Quignard, 1990 : 598)也就是说,如果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确定的意义,所有的问题也一定有答案,那么所有的语言行为都将归于失败。 跟19世纪的主导美学不同,当代世界呼吁意义的不确定性。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基尼亚尔通过文学创作来阐释语言何以以及在何等程度上不产生明确的、唯一的、确定的意义。
在基尼亚尔眼中,语言不仅功能不在场,还带有欺骗性,那么语言还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存在之家”吗? 应该说,基尼亚尔否定和质疑语言,但他的否定和质疑具有生产性和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语言仍带给世界意义,只不过这意义是超出的意义,是意义的缺失。
二、失去的获得,获得的失去
在基尼亚尔看来,语言——获得之物——的本质,决定了语言随时可能跟讲话者分离,词语随时可能消失在每一个人的嘴边。 语言的原初跟产前世界、出生创伤和经由母亲嗓音获得紧密相关。 人自出生就跟母体分离,出生即分离是基尼亚尔作品中不断复现的主题,分离意味着离开原初世界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进入“最后的王国”。 出生导致原本的整体成为碎片:“出生不是开始,而是世界的改变。 这只是旅途的一个边界。 我们从连续性转换到非连续。 我们从‘主’体过渡到‘个’体。 ”(Quignard, 2002: 194)
跟其他学者的观点尤为不同的是,基尼亚尔认为,语言在产前世界就已经存在,我们一直在母体中听到语言。 而且,母亲的嗓音即语言永久性地留在孩子体内,作为孩子-母体之间原初整体性的象征。 跟母亲的嗓音一起永久留在孩子体内的,还有语言创造的一切,包括身份、自我、欲望等等。 基尼亚尔用“被割喉的喉咙”来指称获得语言和摆脱语言之间的张力:“每个人的‘我’不仅不确定,而且是分离的,借用的。 这个‘个体’来自女人的性器官。 这个‘自我’只是语言的回声,语言是他‘先’人的语言,他跟‘先’人获得语言的方式毫无差别……”(Quignard, 2005 : 96)
语言作为后天的纯获得,无法摆脱他人语言、所接受的教育、日常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简言之,个体语言只能源自于他者的语言,缺乏独特性。 如果把出生比作一张白纸,他者的嗓音在白纸上面早已写下姓名、特征、命运等等,也就是说,对孩子而言,永远都不可能摆脱母亲的嗓音。 在这个意义上,获得语言意味着失去,失去“最初的王国”,并在失语、遗忘或临近死亡时失去语言。 另外,获得语言也意味着获得身份,获得不确定的、虚构的身份。 根据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我”是他者语言的建构,基尼亚尔则进一步指出:“身份是家庭滴入的寓言。 ”(Quignard, 2005 : 100)在此,作家用动词“滴入”生动地再现出身份语法建构的缓慢过程。
对孩子来说,获得语言意味着进入社会,同时意味着失去个体的独特性,获得社会归属和同一性,获得跟其他人别无二致的身份。 但是,如果想摆脱这个身份,拥有独特的嗓音和自我,就需要脱离所获得的语言。 也就是说,获得语言和使用语言之间产生某种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就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提到的语言-言语之间的张力,或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所认为的言语-话语或符号-语义之间的对立。 这种张力或对立,在基尼亚尔笔下,变成反抗,用以反抗语言本身,反抗语言的意义,反抗语言作为权力所汇集、所强加的形式或影响。 换言之,基尼亚尔试图跟以往的文学决裂,他想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而远离集体声音。
“渐渐地每个人开始‘相信他的像似性’。 同样,某天,每个意识开始相信,我们通过他人对我们身体的命名而获得身份。 然而,信仰就是对名字的呼唤做出回应。 对于这个奇怪的信仰,我们可以是不信神的。 ”(Quignard, 2005 : 117)作家用形容词“不信神的”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母语的蔑视和反抗,渴求远离由母语而获得的自我,通过蔑视、反抗、决裂,脱离社会的、文化的、身份的关联,而获得新的自我。
“作家角色归于社会决裂和对冲动个体化的征服。 ”(Quignard, 2005 : 125)基尼亚尔用冲动(pulsion)这个典型的心理学术语强调“集体的我”跟社会决裂,成为“个体的我”; 并指出作家需要或应该质疑、超越以往的写作模式,逃脱过去的控制。
基尼亚尔的小说人物大多逃离过去,过着不可见的生活:《世间的每一个清晨》(Tous les matins du monde)的主人公圣科隆布(Sainte Colombe)在夫人去世后拒绝国王的邀请,把自己关在桑树枝叶丛中的棚屋里,全身心投入音乐之中; 《罗马阳台》(Terrasse à Rome)中的莫姆(Meaume)把“一张丑八怪的脸藏在意大利拉韦洛城之上的悬崖”; 《符腾堡的沙龙》(Le salon du Wurtemberg)中,施诺涅(Charles Chenogne)在经历家人、好友离世后,退居到童年的贝格海姆(Bergheim),记录,幻想; 《阿玛利娅别墅》(Villa Amalia)的主人公安娜·希登(Ann Hidden)发现男友情感背叛后,彻底离开之前的生活,“把一切都抹去”。
基尼亚尔认为,逃脱过去意味着离开奴役,通过跟过去决裂而获得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自由。 应该说,其他人也能够像基尼亚尔笔下的人物一样拒绝规划生活的奴役,“但在其他地方的生活真的会令人专心致志吗? 会更有利于创作吗? 彻底的孤独真会是一份鲜美的甜品吗? ”(基尼亚尔,《阿玛利娅别墅》:67)也就是说,创作是否意味着必须割裂社会联系? 意味着必须自我放逐?
针对这个问题,基尼亚尔指出:“圣托马斯用了abalietas(变异)这个词。 他想以此说明,从他人而生的、建立在他人之上的、受他人教导的每个人类造物都只能ab alio(根据他人),只能根据一种顽强的相异性的意愿和偶然性而运行。 我们仅仅是些衍生物; 语言,身份,躯体,记忆,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衍生出来的。 我们身上的我(ego)的建立,比起通过他人的也就是ab alio的起源、家庭的传递 、社会教育、习惯传统、道德宗教、语言服从来,呈现出更多的脆弱性和更少的容积。 ”(基尼亚尔,2007:125)
通过对abalietas的论述,基尼亚尔思考作家、艺术家的身份和地位。 他发现无论是17世纪王家港(Port-Royal)的冉森派隐修士,还是沉浸在书本中的读者,都能够在个体声音和集体声音中选择前者,远离社会生活,放逐自我,离群索居,在自我选择的王国中安顿下来,安顿在这里具有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重要意义,“只有在那间草屋里他的灵魂才是完整的,只要一走进那间草屋,就会对创作充满信心。 他就是在那儿,……创作了他那些最美的作品。 ”(基尼亚尔,《阿玛利娅别墅》:63)
基尼亚尔认为 “人类生命依赖语言,如同箭依赖着风。 ”但是,即使我们是他者的创造物,即使我们无法完全放弃语言、身份、文化和母亲的嗓音,我们可以拒绝以货币和服从为基础的权力形式,以沉默的方式“远离语言和社会”,而“不远离性爱和死亡”(基尼亚尔,2014 : 70),选择拥有灵魂的秘密生活。
1994年,“向往沉默、安静和含蓄”的基尼亚尔辞去一切社会职务,远离社会活动,潜心阅读和写作:“为什么在1994年4月的一天,当天气晴朗时,当我走出卢浮宫时,我突然加快了步伐? 有一个加快了步伐的人穿过了塞纳河,他看着……他跑过去……他一下辞去了身上所有的职务。 ”(基尼亚尔,2007:145)在这则小型自我虚构中,主语人称代词从第一人称单数“我”转换到第三人称单数“他”,“卡夫卡曾惊讶地、满怀喜悦地指出,当他能用‘他’来替代‘我’时,就走进了文学。 ”基尼亚尔通过人称的转换再现生活和虚构的连续性,“我”作为作品人物扩大到普通个体。
如果说,在《游荡的影子》中,仍然能够读出基尼亚尔对集体生活的服从,在彻底辞去所有职务后出版的作品中,作家则明确地表示拒绝集体指令,远离社会生活和语言,抵达沉默:“我来,我出发。 我重新出发。 再次出发。 我在一片黄色的荒原之上建造出新的居所。 /我的生活,曾依附于幸福和认可的生活,摆脱约定的价值的束缚:岁月的不可预见,灵魂的暴力,远离世界的欲望,沉默语言的跳跃,粗野的独立,比自由更加嫉妒的,更加可疑的,更加难抵达的地区。 ”(Quignard, 1995: 197-198)
三、从缺失到沉默
作为纯获得之物,语言极为脆弱,随时会造成缺失,基尼亚尔指出:“我所指称的缺失是所有人的共同体验。 其特点在于完全不可言说,在于我们身上有完全不可言说的具体经验,作为命运的语言获得和死亡的不可言说,……”(Quignard, 1993 : 63)也就是说,遗忘、变声、死亡等情况会造成词语的消失,这是因为任何言语都是不完整的,语言的不完整和限制促使基尼亚尔从事文学创作,写作是作家对抗语言-私敌的最佳方式。
基尼亚尔指出:“作家选择自己的语言,而不被语言控制。 跟孩子相反,作家不服从于语言控制,他脱离语言控制并进行写作。 ”(Quignard, 1995: 15)也就是说,作家通过质疑、对抗母语来控制语言。 由此,基尼亚尔的作品在语言的边界游移,词语在他笔下从习惯用法中跳跃出来,往往多体裁并置,呈现出碎片化和不连续性等特征,成为“不确定叙事”或“不可论述的写作”。
因此,基尼亚尔作品无法进行传统意义的分类,体裁的无法判别正是其创作的鲜明特征,也就是说,与其探讨体裁问题,不如对具体文本进行处理。 在一次访谈中,基尼亚尔拒绝对小说进行定义,他说:“它(小说体裁)是所有体裁的另一个,是定义的另一个。 跟体裁还有普遍化的东西相比,它是去体裁,去普遍化的。 在存在‘一直’的地方,放置一个‘有时’,在存在全体的地方,放置‘个别’,这样,您开始接近小说。 我能带给您的,是弦乐器制造者的定义,是知识的定义。 ”。
另外,基尼亚尔认为语言缺失是行动的源泉,而语言缺失适合于音乐家、孩子和作家:“在语言中,作家被简单地定义为stupor,导致大部分作家是口语的被禁止者。 ”(Quignard,1993 : 10)基尼亚尔自己曾经历两次失语:“我曾两次失去语言。 18个月时,我不讲话……童年时的抑郁状态发生在我们搬到勒阿弗尔之后,当时母亲卧病在床,而一直照顾我的一位年轻的德国女人离开了我。 我叫她Mutti。 我变得缄默不语。 ” (Quignard,1993 : 59 et 61)德语中Mutti的意思是母亲。 这个年轻的德国女人的离开,让基尼亚尔经历第一次沉默。 作家第二次失语发生在16岁,他对于这一次沉默的原因选择闭口不提。
基尼亚尔对他所经历的两次失语进行重新建构,他认为在重新建构语言中,一切都是虚构。 也就是说,失语,语言缺失是个体无法逃避的命运,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作家必然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失语者。 ”“写作的人目光集中,身体一动不动,手伸向前方,朝向逃离的语汇。 ”(Quignard,1993 : 12)而写作的手寻找语言的缺失。
写作即寻找,是作家的生命需求:“我不因欲望、习惯、愿望、职业而写作。 我写作是为了继续活着。 我写作是因为这是沉默言说的唯一方式。 沉默言说,无声言说,寻找缺失的词语,阅读,写作,是一回事。 ”(Quignard,1993 : 62)写作能够在沉默的同时言说,能够在表述的同时保持沉默。
什么是“沉默的言说”? 柏拉图(Platon)在《斐多篇》(Phèdre)中明确指出,文学是沉默的声音。 基尼亚尔认为,“沉默的言说”是写作的原初,因为文字是沉默的,而且一直不变,无法表达世界的变化,另外,写作者对其读者一无所知。 因此,写作造成分裂,阅读不是交流,最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也不是交流。 柏拉图曾预见,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阅读会变成孤独的行为,而隐藏在语言沉默中的作者跟诡辩家差不多,都是不出现和不真实的人。
而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则区分朗诵话语和神圣话语,认为后者更接近写作:“跟神圣话语相同,被书写的东西来自我们未知的地方,既无作者,也无原初,因而朝向更原初的东西。 ”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其《沉默的言语》(La parole muette)中,提出小说是“无体裁的体裁”,“自古代文明起便开始承载沉默-多语的文学权力。 ”朗西埃判定写作是多语和沉默的书写。
由此,从柏拉图到布朗肖、朗西埃,再到基尼亚尔,都“试图使语言解除约束。 试图打断对话。 试图不服从驯服。 试图摆脱兄弟姐妹和祖国。 试图摆脱所有宗教。 ”(基尼亚尔,2007:117)概言之,文学就是沉默的言说:“与说话不同,写作止于沉默,它的语言在个人眼睛下变成沉默之物。 写作者所寻找的,不是通用语言世界里飞翔的、不可见的符号。 在语言的彻底沉默中,在与之相对的完全可见的语言面前,灵魂远离秩序,在符号周围、在空白周围、在声音的远方,到处搜寻。 它思考着既非言说又非意指的另一种事物。 而这另一种事物,就是文学。 ”
语言方向评职知识:好投稿的语言学期刊
结语
作为出身于著名的语言学世家、接受过传统严格的语言学教育、对语言问题持续思考、并潜心从事语言工作(阅读和写作)的当代杰出作家,基尼亚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探寻语言的原初和本质,最后,通过文学创作,通过沉默的言说,对抗语言这个私敌,将有声的语言化为无声的文字,让“语言到达他未知的地方,抛弃社会的、分享的、奴化的语言; 他要创造出差别,并自我隐退。 ”
作者:刘娟
SCI期刊目录
SCI论文
- 2024-04-29尝试投稿Nature、Science顶刊,
- 2024-04-29英文论文Editor Assigned一般多
- 2024-04-29Advanced Science算顶刊吗
- 2024-04-29sci期刊投稿系统要勾选预印本吗
SSCI论文
- 2024-04-22ssci期刊分区怎么查
- 2024-04-18ssci论文更快接收的技巧
- 2024-03-27SSCI二区论文有什么快速发表的办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EI论文
- 2024-04-22土木方向国际会议发论文难吗
- 2024-04-17电气电力方向2024年的学术会议
- 2024-04-12EI会议发表文章的流程
- 2024-04-12真空、陶瓷、绝缘方面的会议怎么
SCOPUS
- 2024-04-15SCOPUS检索的会议怎么找
- 2024-03-23Scopus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属于什么
- 2024-03-14scopus论文着急见刊怎么弄
- 2023-12-25艺术教育论文可以发到scopus吗
翻译润色
- 2023-05-13神经生物学英文文章如何提升英语
- 2023-05-12sci论文润色的意思
- 2023-05-11生物医学sci论文润色有用吗
- 2023-05-09锻造相关中文文章怎么翻译为英文
期刊知识
- 2024-03-21论文发哪些期刊符合评高级职称要
- 2024-02-21论文发国际期刊的五大优势
- 2024-01-13英文、中文期刊傻傻分不清楚?这
- 2023-12-20地质比较好发的期刊
发表指导
- 2024-03-06哪些食品类期刊被ei收录
- 2024-02-29图书资料副研究馆员职称有学术专
- 2024-02-23准备评正高需要什么学术成果
- 2024-02-22论文发英文期刊原始数据包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