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期知识分子的“回归”与“超越”贾植芳四十年代思想探求
时间:2022年01月13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作为“五四”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贾植芳的人生形态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作为“社会上的人”,贾植芳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独特观察,带有明显的“鲁迅—胡风”主体论思想的印记。贾植芳的思想不止于控诉社会的丑恶和重塑政治秩序,更是要张扬个体生命形态,保持高贵傲骨的文化品格;他在实践中秉承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以主体精神投入社会实践;他批判“生命的零余者”,高扬“寒夜中的热力”,形成了“超越”的人生。
关键词:贾植芳;人生形态;回归与超越;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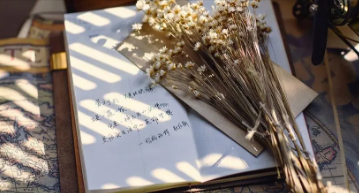
1936年至新中国成立前,是贾植芳从“文学中的人”到“社会上的人”身份转变的一段历史,也是他思想成型的重要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贾植芳文学活动密集频繁,除了协助胡风编审稿件、主编杂志《青光》外,还结集出版了小说集《人生赋》①、散文诗集《热力》②。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贾植芳遍尝各式牢狱生活,见识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违反了国民党政府《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而被北平警察 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关押两个多月;1945年5月,被日伪警察局特高课以“策反罪”逮捕,关押三个月;1947年9月,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以“煽动学潮罪”逮捕,关押一年有余。
1948年9月,贾植芳被保释出狱后写就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和中篇小说《人的证据(在蒋匪特务机关监狱中的回忆)》。在历史的沉闷期,以贾植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仅要面对40年代国民党政治混乱崩溃的局面,从50年代起,开始接受我党的思想改造和规训惩罚,在政治权利的历次“合理化”场域中逐渐退场。我们需要将贾植芳40年代的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思考,思考贾先生在“社会”中的人生形态,进而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回归”与“超越”的历史命运,这对于构建新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是有重要意义的。
1走向“社会”的五四青年
“五四”之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帝制复辟等成为基本的“社会”现状,士兵的枪炮和宣传的笔舌则成为“社会”的言说方式。“社会”呈现出压倒文学的倾向,主要表现就是忽视甚至否定“五四”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和个人生命形态的内涵。20年代末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转换方向”,就是将“个性”“自由”等五四思想转变为“留声机器”的革命思想。
30年代初,瞿秋白认为“五四的娘家是洋场”,五四是半路的失败,因而需要再一次革命。[1]339这样,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形态规训了五四思想中以“个人”为核心的生命形态,也容易使知识分子患上政治冷漠症,甚至其中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犬儒。为此,贾植芳将这种历史现象称为知识分子的“回归”现象,并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五四”的文学先锋郭沫若,“早先写《女神》,讲个人主义,反叛得不得了,最后却转回来,拥护一些原来他自己批判过的东西”[2]190。
一个是20年代北大新潮社,学生运动出生,却在成为国民党高级干部后,镇压一二·九运动的一群人。他们“一代闹一代,自我否定,走向自己的反面”[2]190。贾植芳认为,这两类人的共同点在于都以新的社会形态收编和约束个人的生命形态,丢掉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从而很难保持独立的文化姿态。在思想谱系上,贾植芳更倾向于“鲁迅—胡风”思想序列,坚持将国民文化心理结构剖析放置在个人生命形态的核心位置思考。
譬如,鲁迅早期思想中有“任个人而排众数、拾物质而张灵明”的观点,后期转而剖析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国民根性,根本在于“人性至于全”的探讨。胡风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继任者,他坚持将个人解放的前提理解为“主观战斗精神”,坚持个人生命形态至上主义。基于以上情况,以贾植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恰恰是一群走向“社会”的五四青年们。首先,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往哪里走”,是选择“个人启蒙”继续营造“纸上的事业”,亦或是转向 “社会运动”承受革命的张力。“往哪里走”的问题,关涉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贾植芳这样自评:“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上的人。”[2]7与贾植芳先生过从甚密,对他了解最深,而且是他一生挚友的胡风也认为贾植芳是“东南西北走的人”。在我看来,“学问人”和“社会人”是贾植芳文化身份中对等的两个方面,而不是排斥关系。首先,贾植芳侵染着“五四”的文化精神,受鲁迅影响颇深而形成“学问人”。“五四”和“青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贾植芳认为自己是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3]15。
留日期间,鲁迅的去世对贾植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贾植芳不仅写作悼念诗《葬仪》,而且还参加了留日中国学生各团体举行的鲁迅追悼大会。此后,贾植芳又将小说《人的悲哀》投稿胡风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我从它的编辑风格和撰稿人员阵营中,惊喜地发现这是坚持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战斗文学旗帜的严肃文学刊物”[4]264。这篇小说是典型的鲁迅式“遵命文学”。贾植芳着力营造了带着浓厚“五四”气息的沉闷“社会”,充满了“令人弯腰屈背的物质和精神的重压”,“青年”在混乱而沉闷的社会中寻求个人的思想启蒙和社会的文化重塑,“无声”的街道、愚昧无聊的市民与“羊吃羊”的景观构成了对社会的文化批判。
“悲哀”的艺术氛围表现了“青年”在追寻“主义”话语之后“文学梦”的破碎。理解贾植芳的身份问题,就不能离开五四“青年”这个关节点。虽然他曾笑谈自己仅仅是文坛上的散兵游勇,文学创作也仅仅是黄浦江里的一泡尿,没什么影响,但五四“青年”的身份却成为贾植芳观察30年代中国社会病态面貌的文化习惯。于是,我们很容易发现贾植芳作品中在“历史的惰力”中丢掉灵魂的病态国民群像:疲惫而无聊的营生者(《人生赋》)、蠕动而迷惑的聒噪者(《剩余价值论》)、愤世嫉俗的幻想者(《理想主义者》)等。其次,贾植芳并不认为自己在经营着“个人的文字事业”,而是一位逃避“作家”身份的政治犯。
“30年代,正是中国深受内忧外患、困扰最严重的时候,从国际大局看,也是世界上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仰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左倾’成为世界性时代思潮的时候,我由于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接受了这股时代思潮,又受地下党的启蒙和影响,由文学观念的确立到投身社 会运动,由报纸的文学投稿者变为‘政治犯’。”[2]5值得关注的是,贾植芳这种“姿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要素:十月革命、左翼思想、社会运动和“政治犯”。前两者构成了中国“社会”30、40年代的基本面貌,后两者则构成了贾植芳的社会实践。换句话说,贾植芳的自我“身份”是以中国“社会”为限定的,因为有了“社会”意识,他才能摆脱五四的“浪漫”气息而多一些实践色彩,也才能不囿于“纸上的事业”的营造而尽到自己的人生责任。
“人”不是安坐于客厅与沙发间,成为一名纯粹的文章书生,而是要在人生的旅途中思考社会,着意于“把人字写端正”。即如他后来在《热力》后记中谈到的:“我是一个偶然拿笔的人,虽然这点兴趣也增加和鼓励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但处在这样的时代里,它也给我带来更大的愤懑和悲哀……这工作可说是一种‘逃避’,而就是这样可悲的‘逃避’,还是不容易逃避的!”[2]299可以说,贾植芳40年代思想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对社会悲剧状态的理解和认识是以鲁迅—胡风一派张扬个体生命形态来承担的,存在着一种形而上的主体哲学———即在“社会”中“把人字写端正”。
2历史实践中的“社会”观察
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五四青年在40年代与“社会”形成的实践关系及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生形态的影响。1936年9月,贾植芳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科,随后,进入社会科专修班,师从园谷弘学习社会学。对于转学社会学,贾植芳认为社会学学生身份可以暂时“政治避难”,同时,在文学创作上也可“获得观察、分析社会的基本方法”的导引。[4]15在日期间,贾植芳积极介入社团,参加了一些颇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如左联东京支部组织的悼念高尔基的活动和东京留学生各文化团体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追悼会等。
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进程的急剧变化,促使“青年”走出书斋,思考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进而勾勒蓝图重新建造当代民主社会。“青年”的文学梦破碎了,他们抛弃了“五四”时期的“主义”,成为国家的政治家。这种关注点的变化,也带来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青年”转变为“政治犯”。“青年”发现了社会中的个人价值,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批判传统旧道德,可以说“青年”的反抗多少带有思想家的魅影,而“政治犯”思考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思考“社会”中“恶”的根源,其根本 指向在于检讨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向。
简言之,“青年”的道德关注限于自我,“政治犯”的政治关切在于制度。这样,作为“政治犯”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形成了实践性主体关系,肯定他们的主体地位,就在于重新张扬他们独立的文化姿态和人生形态,而不是将他们看成“社会”中没有血肉的玩偶和阶级政党的附属物。贾植芳将4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称为“史前时期”,抨击了社会中“精神世界的谑画。”[2]
265国民政府的统治本能在于通过监狱管教保持其权利的合法化,但其政治上的衰败却导致了暴力行动的合理化,监狱“风景”成为一种能够表现政治阴暗与衰败的“文化实践”,成为政治权威崩溃的写照。在这样的监狱牢笼中,“政治犯”复归为自由的人就在于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发现世界。于是,以贾植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被捕入狱以及对监狱生活的观察都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质,这是对一个极端政权的公诉状和抗议书。
在贾植芳看来,监狱是国民政府保证其阶级统治的强制工具,国民政府权利的衰落以暴力的形势展现出来。在这里,政治犯的生存被摧毁着,个体的生命被当做燃料,推动这个腐败的国家运转着。暴力并没有将这些政治犯的世界观改造,反而破坏了政治犯认可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使国民政府丢掉了国家理性和合法的统治认可。在《在亚尔培路二号》中,老蔡对特务机关的观察是很康德式的,“这真是一个标准的国民党式的机关,……他们很明白他们作坏事的意义,而且加倍努力去作,”监狱的生活是恐怖的,这些政治犯虽然遭受了老虎凳、绞头、挟指甲,会发出“非人间的声音”[4]227。而在另一部小说《人的斗争》中,贾植芳塑造出了狱卒的群丑图。
“野兽”对“人”的审问虽然是有“修养”和“害羞”的,本质却充满着“兽”的逻辑。“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不给他下手,要是有证据而不认账,这是和我们为难,这最不可原谅!”[4]239贾植芳进一步将对“社会”的观察上升到哲学层面,即“黑夜”哲学。“对于过惯黑夜生活的人,早晨在他是一种发现、惊奇、忏悔和感奋,……使生命蒙上黯淡或不洁的色彩,造成人生的歧路和损失———无从补偿的损失,除非来生可赎愆的损失。”[2]
251这是《热力》的开场白。贾植芳将“黑夜”想象为40年代的中国社会,不在于对“黑夜”的自然摹写,而在于“黑夜”所“装置”[5]12的主体对于“社会”的认识和判断,“黑夜”是“喧嚷或死寂”的,亦会造成“艰辛,喘气,疲倦和战栗”,“黑夜”于人的生命造成了一 种压抑的存在。作为存在的“人”,只有“击败考验的创造、跨过死亡的征服,和蔑视一切污秽的占领”才能完成“人”的意义。
因而,贾植芳对于“黑夜”的颂扬是以“人”为叙述目的,“黑夜”绝不是人的世界,它是对人生健康的生命形态的否定,它带给“人”的是心灵世界的焦虑,这种焦虑不是疲倦和恐惧,而是文化上悲烈的“战士”精神。贾植芳试图让“人”对“黑夜”保持战斗的姿态,在非人的社会境遇中自我超越,才能发现“早晨的伟大和美丽”,“人”的主体意义也才能获得超越。其实,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观察往往会形成两种主体观念:遵命与不遵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兵”的社会形态规训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个体生命形态,文艺活动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等,这样的逻辑必然会导致知识分子政治命运的“交华盖运”。遵命者,可以得来国家政治层面的崇高荣誉。而那些依然顽固的坚持人的主体性高于阶级性的作家则被视为不遵命者,往往命运多舛。联系贾植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他是一位积极的不遵命者,而不是消极的不遵命者。贾植芳没有在历史漩涡中把政治审判看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是尝试着走出“政治犯”身份的心理障碍。对于那些附属于政治的人格,贾植芳认为他们是“悲哀的玩具”,等待他们的是历史清道夫无情地审判和清扫。
3知识分子的“超越”
面对40年代的“社会”现状,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保持怎样的人生形态呢?1946年5月,贾植芳在徐州先后两次致信胡风,“在这样闷塞的地方活着,是只许动物式的营生的;住久了,会使你变成一个虚无派,好像回到我们祖先们的洞穴中一样,是这样的可怕”[6]24。一周后,他又致信胡风:“近来心境颇暗淡,以至于要写的上海游记,写过扯了,扯过又写,到现在还没写出个所以然来。”[6]
24在此之前,胡风曾与贾植芳谈及重新开展希望社活动和出版《希望》杂志的设想,贾植芳徐州之行的目的便是为刊物筹措资金。贾植芳在信件中流露出的苦闷心焦,恰好传达了他对上海复杂的“历史心情”:如何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持自由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操守。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之外,还在于贾植芳并非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来看待这个战后动荡的社会,而是以“社会上的人”的主体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个体命运和责任。
1947年,贾植芳应《学生新报》“五四征文”邀约做杂文《给战斗者》,“想起了我们还得用战斗去纪念‘五四’;以鲜血纪念‘五四’所流的鲜血,多少感到悲愤”[2]297。贾植芳对上海社会现状的思考是以“五四”精神为衡量的标尺。“五四”时期“自我”发现是以拒绝社会的“闷塞”状态为前提,“自我”的确认必须要对社会有责任的担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贾植芳世界中的“自我”不仅仅包含了“五四”时期世俗的“人”,而且还糅合了“战士”的影子。
首先是清除“趣味”。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带来的文化冲击、洋务运动形成的商业氛围与独特的海派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使得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最为发达的公共领域。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旧文化思想的交锋依托《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展开,而战场则是摆在上海,“支持文学研究会的商务印书馆和支持创造社的泰东书局都设在上海,形成代表新文学主流的作家群,而鸳鸯蝴蝶派文人则转移阵地,垄断上海的小报副刊、通俗杂志、电影戏曲、连环画报、无线电台”[7]223。
可以说,“五四”时期的上海是“动起来”的。然而,40年代的上海则稍显寂静和黯淡,社会充满了“外国绅士淑女的闲情逸致和消愁解闷”[8]388。胡风的“趣味”针对的是战后上海社会所表现出的一种低级庸俗的文化倾向。贾植芳则将“趣味”进一步理解为“动物式的营生”。于是,在散文集《热力》中,贾植芳塑造了许多“非人”的形象,如《魔术班子》中的走兽们迎接着“绅士淑女模样的上等人”和“穿各色制服的人物”的赏光;《窗外》喧嚣的狗子们以及《夜间》沉闷的黑暗院子里与失掉人性的僵尸的斗争。在他看来,“非人”意味着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的苟且生存,丢掉了反抗的“思想体系”,破坏了社会的善恶之分,无法担负起再造社会的重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带着“五四”的浪漫主义理想,却被中国30、40年代紧张的社会现实甩出,丢掉了民族和国家的责任,而以个人利害为行为标准,导致了“非我”的产生,或复古读经,或政界周旋,或下海谋利。与“趣味”相对,贾植芳和胡风都谈及“人”(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该具有的生命形态。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存在着畸形和残缺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期间,通过阶层的划分,“社会”确定了专政、抑制和团结的对象。而那些超越了历史与自我、拥有清醒健康的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往往会由于“不遵从”而接受“社会”的规训。
于是,历史中就充满了荒诞而粗暴的政治审判,充满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尚人格理想的文人被劳教改造,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品被送进历史的熔炉,与此相关联的则是知识分子被扣之以“反动权威”“监督对象”“阶级敌人”“臭老九”等帽子。然而,以贾植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却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超越”意识,没有将文学事业功利化,没有推脱历史责任和道义承担,没有在权力赋予的“自由”面前失重。贾植芳将人的尊严、价值和责任有机地体现在他并不顺服的“爆炸”人生中,而这一切的落脚点都在于贾植芳的“超越”意识。
参考文献
[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3]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4]贾植芳.贾植芳小说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5][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第1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7]贾植芳.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8]胡风.胡风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孙军鸿
SCI期刊目录
SCI论文
- 2024-04-24sci论文审稿结果一人拒稿一个接
- 2024-04-24Journal Of Zoology 杂志发文范
- 2024-04-24sci期刊投稿版权转让协议怎么弄
- 2024-04-22食品检测方向sci期刊选择方法
SSCI论文
- 2024-04-22ssci期刊分区怎么查
- 2024-04-18ssci论文更快接收的技巧
- 2024-03-27SSCI二区论文有什么快速发表的办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EI论文
- 2024-04-22土木方向国际会议发论文难吗
- 2024-04-17电气电力方向2024年的学术会议
- 2024-04-12EI会议发表文章的流程
- 2024-04-12真空、陶瓷、绝缘方面的会议怎么
SCOPUS
- 2024-04-15SCOPUS检索的会议怎么找
- 2024-03-23Scopus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属于什么
- 2024-03-14scopus论文着急见刊怎么弄
- 2023-12-25艺术教育论文可以发到scopus吗
翻译润色
- 2023-05-13神经生物学英文文章如何提升英语
- 2023-05-12sci论文润色的意思
- 2023-05-11生物医学sci论文润色有用吗
- 2023-05-09锻造相关中文文章怎么翻译为英文
期刊知识
- 2024-03-21论文发哪些期刊符合评高级职称要
- 2024-02-21论文发国际期刊的五大优势
- 2024-01-13英文、中文期刊傻傻分不清楚?这
- 2023-12-20地质比较好发的期刊
发表指导
- 2024-03-06哪些食品类期刊被ei收录
- 2024-02-29图书资料副研究馆员职称有学术专
- 2024-02-23准备评正高需要什么学术成果
- 2024-02-22论文发英文期刊原始数据包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