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以象外的畅想与神思——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艺术思考与实践
时间:2020年04月20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一、精神的远游“超象”,作为艺术命题提出伊始,经过从古至今的奠基、扬弃、生成与绵延,已然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理论概念和艺术实践的探索课题。“超象”是当今世界艺术发展新思维、新观念的必然历程。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探索,都是基于国际文化视野、华夏文化复兴的意识,来高度把握并应对世界艺术的新格局、新变化,力图以“超象”这一精神性艺术标志的确立,推进现代水墨艺术的发展,赋予水墨艺术以新的生态伦理价值和美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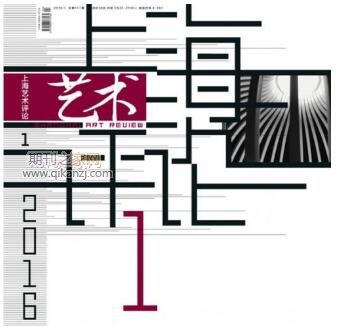
“超象”概念源于我国古代艺术思想。早在唐代,司空图就在《诗品》中提出“超象”概念,即“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离形得似”等等,用以指涉取之象外,略于形色的思维特点和艺术表现方式。作为中国艺术最高境界和最高精神目标,“超象”令艺术家及其作品不断向心灵靠近,并远离自然与世界的形而下特性,不断地打破物与我的二元对立,使之契合,最终实现和谐统一。“超象”的提出及其在艺术实践中的运用过程始终以人为主体,体现为人之自由意志的觉醒和艺术精神的觉醒。
“超象”的“象外之象”“略于形色”“取之象外”,是由此及彼,由显而隐的提升与深入的过程,强调一种由内心意绪向生命情怀与精神境界的转换,进而在趋于抽象却又具体可感的艺术形态中,领略一种陌生化的玄妙意味,这是一种超验的审美感觉。与此同时,绘画材料与手法亦在“以技入境”中被赋予高度的意义与内涵。诚如我在自己作品《超象》系列中所表现的结构、节奏与虚灵,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呈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象外之象”的抽象效果。
当然,对于“超象”的理解、把握与运用,是因人而异的,在艺术家那里,它往往是在完成内在自我本质的转换之后而见诸于作品的。天地有大美而无言,事实上,对“超象”的取舍及态度的亲疏,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观、艺术观和人生观,乃至生命体验、审美经验与精神境界,在这种特定的无言之美中,体现的则是人的精神自由与情性率真的玄思与遥想,在绘画中,则呈现为一种不可言说的幽玄秘境和精神远游的神秘。这是难以用常规符号、技法去固定表现的,它们或浓郁,或淡然,或清丽,或雄浑,其色彩、形态的流变,激发与幻化,展示的正是“超象”那难以测度的高风远韵。
质言之,“超象”的关键与根本之处,首先是一种对物性与形象的超越,这是一种向三维空间之外的更大境界的超升——对宏观世界、对生命幽微本质的抽象性把握。因为,任何本质性艺术的运动与把握都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追寻与发现,是从形质世界向性灵世界的过渡,也必然是一种脱略形迹的提升与超越;而且,唯有在此中,才能表现出其深奥之处,显示其最微妙的所在,并超越现象而走向纯粹与永恒。在这里,艺术法则、规矩、范式、理念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超象”的突破中表现智慧、灵性、才情、气质、格调、能力。
此外,由于它的纯粹性和元初本真的特点,一切外在的、附加的、雕琢的、世俗的、伪装的成分都被统统剔除和抛弃了。因此,它表现出来的乃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也是更自然的风格品质,展示出的则是内在的智慧、自在的精神、宏观的视野、脱俗的风度,这便是“超象”的风采和韵致,也是一种审美重心的转移。
绘画创作中的“超象”经历了一个从生命之冲动到天地运动、灵性之气韵,再到造化之气韵的转化过程,最终合并一体并将它集中在色彩、笔墨的挥洒、运作之中,使之“得其神而遗其形,留其韵而忘其迹”。在看似随机无意的泼、洒、挥、滴与叠加、覆盖、错置当中,体现出的都是画家胸有成竹的匠心独运。细细看去,在漫漶氤氲的画面中,在如同风云际会、惊涛拍岸的墨色形态中,体现出的都是出自画家生命力的充沛和昂扬,其中蕴含着支撑动感画面的稳定结构。
与写实、摹仿风格的绘画相比,这是一种风格的巨变,也是对传统审美旨趣的转化,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今人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对“超象”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发现。从根本上说,这是灵性十足的精神运动外化为飘逸、灵动、洒脱的形态,它表现的不是现象世界本身,而是关于世界可能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精神图景,这是一种境界,让人身不由己地感受到自然生命气韵的变异和澎湃。“超象”之后,结果必然如此。简而言之,“超象”作为艺术概念,有这样的特点:它以体验和感悟为内涵,并形成特点,趋向于宇宙论、价值论乃至生态美学的追寻和叩响。它以宇宙运动形式为内在结构,强调创造性活力、活跃的生命精神、和谐的形式内涵和浩荡无垠的诗境。它强调个人的主观灵性和内在价值,并在价值范畴与本体范畴上肯定“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终极境界——“超象”的图景。
二、心灵的印迹“似者,得其形而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荆浩在《笔法记》中,对绘画的“似”与“真”做了本体意义的区分。“似”,指表象的相似,它缺乏内在生命结构与本质之处,仅止于“有形无神”而已;而“真”,则包含了事物的内在生命气质、结构与气韵,所以,它充沛、丰满而又神采飞扬。后者正是“超象”特有的本质之“真”,它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赋予事物以无始无终的超越性逻辑关系的形态,并在三维空间之外呈现其神奇魅力;所谓“超象”,是一种超越表象的本质意义的“象”,是事物的终极存在,它展示的是终极的创造与心灵的印迹,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艺术形式、结构与语言。
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超象”不只是审美问题,作为心灵印迹的表现形式,它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精神与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在今天,“超象”已不再是古典艺术的自律,而是艺术自身价值的体现,是对传统审美定式的解构,因此,当代“超象”是艺术创造与当代精神共同孕育出的结果。因此,我们重释“超象”,是以反思社会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危机为背景的。现代科技带来的弊端,使得具有生态美学涵义的“超象”审美意识日渐凸显出重要性。
现代技术造成的资源枯竭、土地沙化、环境污染等弊端只是结果,根源在于现代技术与生态的敌对性质。海德格尔在分析“技术”的词源时指出,“技术”在古希腊的本义是“引发”,技术与艺术一样是解蔽的方式、真理发生的方式,而现代技术却违背了其本义,成为一种“促逼”。并非现代技术发展到今天才成为人们无法控制的东西,而是现代技术从本性上就无法控制,它已经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
现代技术不仅造成生态系统失调,威胁着其他物种生存,而且剥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万物贬低为资源。现代技术作用下的人类,不仅把自然界作为能量储存器,而且使人脱离了自己的本源。在这种情况下,“超象”式的审美意识成为对抗生态危机和人性异化的途径。“二战”之后的西方当代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以及精神性艺术的发展,是在重新认知犹太教—基督教的创世论之同时,大量借鉴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诸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有关“生生为易”“元亨贞吉”与“坤厚载物”的论述,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众生平等”等。
这些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生存方式与思维,可以成为我们建构“超象”艺术的丰富资源与素材。因此,“超象”艺术以“天人合一”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相会通;以“中和之美”与“诗意地栖居”相会通;以“域中有四大,人为其一”与“四方游戏”相会通;以怀乡之诗、安吉之象与“家园意识”相会通;以比兴、比德、造化、气韵等古代诗学智慧与生态诗学相会通……我们应该借此来建设一种包含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资源与话语,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某种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超象”艺术体系及其流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超象”的生命活力不仅来自其自身,还来自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反思、判断,同时也来自主体间性的经验和选择,特别是在文化的多元格局中,观念的多样和媒材的多变都使“超象”确立了更具文化现代性的整体艺术特征。我创作《超象》系列作品,力求在传统的“度物象而取其真”的理念中提取并建构现代意义的共享价值与共享空间。实际上,“超象”是一个大艺术主题,在这里,我找到了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并以自我的方式抵达超我。
在《超象》系列作品中,我大体以传统绘画材质为主,宣纸、矿物颜色、墨色、笔和毛刷,同时也混合了外来的水粉、水彩,以及金粉、银粉等颜色,还加入了拼贴等综合手法,使墨、色、水、纸等互相冲撞、融合、演绎、幻化,在无序的流淌中进行局部或整体的控制,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感觉性与情绪化的介入,在水、墨色的氤氲、冲撞中凝定出心灵的印迹,在随机性的泼洒、滴溅中表现出对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现与开掘,让纸上的“超象”再不确定于非具象的形态固化中,体现出自我的作用,揭示出无法复制的精神图像和心灵印迹,揭示出梦幻、虚无的随机性背后的心灵丰富性,以及自我感觉的独特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无意识的泼洒与滴溅中,包含了潜意识下的选择与控制,不同的色彩间的混融,水分的多少,氤氲与幻化,着色处与空白的布局分配,自然形态与人为的描绘,漫漶的流淌与拼贴的形状,乃至色彩的浓淡变化……这些均在没有具体形象的流淌中变成一种状态、一种综合,它的含糊性使我们的视线随着无规则的色墨流淌向画外延伸;泼洒的色墨、滴溅的点、线、面虽没有蠕动,但它的节奏充满了运动感。这样的抽象形式意味及画面结构、节奏、韵律、力度,表现的正是期望中的“超象”图景,也是自我心灵的自然流淌。这种不受约束、不受规范,充满自由与随意性的表现方式的核心是自我情绪的冲动与狂热,它冲破了传统绘画逸笔草草、一波三折的限制,把画面的向心性、平衡特点及构图的完整性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扩散开去。画面更注意力度、强度、节奏、韵律与刚柔的对比表现,这种表现必然传达出画家自我的主观意识。
《超象》系列作品最明显的特点是摆脱了“形”的约束,它们在无形、无序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力量。把大张的宣纸铺在地上,通过泼洒、滴溅,造成风起云涌、惊涛拍岸般的抽象状态,传达着某种潜意识。在密布的色彩流动、纵横交错、氤氲重叠中,那种没有制约的活力与随意挥洒的运动感、无限的空间波动愈发变得狂热而又抒情,这里蕴含着作品生命的关键所在。这是一种原创的心灵图像,它呈现为一种特殊的质感,可谓色墨和谐、动静统一、从容自然、情绪流动、力量内蓄。这是自然流露出、鲜明而又强烈的自我表现,也是独白式的自我表达。
我在作品中要表达的是自己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但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无意识与潜意识的强大作用,我不知不觉地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关注和强调的仍是自我的主观感受,以及语言、材料的独特表现力。当然,《超象》作品既不是传统艺术所能全然表现的,也不是现代艺术所能全然表现的,它是古典的“取意象外”理念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心灵碎片相合互融的结果,进而形成特定的审美空间。在《超象》系列作品中,表现前提不是现实的片段与自然场景,而是从整体去把握并表现自然运动的生命节律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把对自然的感受积累起来,并归纳出它的内在构成关系和相关精神要素,用直觉的方式打开属于它们的潜意识领域。
无疑,这是对其精神要素的肯定,为此,必然要对画面中的时间因素进行消解,变三维空间为二维空间,一切都被平面化,而时间则被空间化,空间笼罩了心理的色彩,使我们得以在同一画面的有限空间中看到多空间的交叠,这是自由的,也是神奇的,画家需要将之转化为逻辑关系和客观规律之外的自由存在,以及更为鲜明的观念性要素。
在泼洒与滴溅的过程中,自我与材质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作品的不确定性、无中心感和无界限感构成了《超象》主题的最显著特点,此时,画面上呈现的是完全自我的方式和一些不由自主的心灵印痕,可以说,在无意识中留下的是生命本身,展示了一个身不由己,但又从容自然的过程和运动轨迹。泼洒与滴溅使画面效果往往出人意王林旭金轮纸本综合材料68×68厘米2005料——大面积的风云翻滚、波涛巨澜、无边无际、鬼斧神工般的形态令人浮想联翩……与此同时,根据画面自身的需要,再拼贴插入局部几何形“硬边语言”,这既增加了平面空间的层次,又丰富了语汇,体现了一种现代意味。
诚如英国学者鲍曼所说“数学是现代精神的原型”那样,这样的创作手法突破了“超象”原来的定义,与现代艺术不期而遇,拓展了其外延与内涵。应该说,这里探讨的重点不是主题本身,而是几何性的形、线、型、块、面、色的成分和内在关系,以及用以造成神秘玄妙的发人深思的效果和张力。《超象》系列作品的基础似乎不再是现实世界和客观自然,而是观念——某种概念的、几何的、建筑的、梦幻的和虚无的。它不仅表现了自我,还在于表现了一种新的视觉样式、一种新的艺术秩序及一种新的艺术理想。《超象》系列的起点发端于东方哲学智慧,同时又是观念与平面空间构成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对尺度的把握,对数学关系构成的把握,因此,它不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也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把艺术当做对超验世界的追求,它是审美自律性的必然表现,也是人堆存在世界主观感觉的表现。
三、流动而绵延的圆融“超象”是可以绵延的宏远存在。西方哲学家柏格森的绵延论与“超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一种精神的运动在拒绝一种存在的同时又构建了另外一种存在。而“超象”之深矣、远矣、不可及矣,则是对所有具象存在的超拔之后获得的,它没有实体,然而却存在;就某种状态而言,否定即是肯定,泯灭即是创造,虚无即是存在,反之亦然。
因此,“超象”具有鲜明的心灵特点,它以虚无为象征,氤氲为暗示,且紧密联系着虚静至极的境界,《超象》系列作品的色彩、笔墨、团块、点线、几何形体等的构成与整体关系便是这样。它不是要表达什么,而是一种暗示,一种隐喻,一种对心灵世界的憧憬,它非具象的泼洒、重叠及整体取向都折射出自我身心的深化、澄化和净化。在创作《超象》系列作品的过程中,我获得了“超象”的启示。同时,我还把我所走过的东西方山水、圣地、名胜、遗迹等融入了写意与抽象的点线、墨色之中,以及画面上色彩的漫漶、几何形状的交叠,构成关系的相互切割……这里面都有我发自身心的感受与体悟,这不是具象逼真的描绘,而是感觉与情绪的凝定,是一种跨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建构与努力。
雪山、圣湖、山峦、流水……这些物象都是“得其神而脱其形”的抽象演绎,而作品的总体气象都是“超象”的启示或“超象”本身的呈现。因此,它的形式、语言与气息是深化与净化的,其抽象的意象便在内心成形,这也是我心灵世界的袒露——素心若雪、独立苍茫、泊淡辽阔、广大精微、熔于一炉。“超象”的理念与我的“超象”主题让我的作品通向了浑茫圆融的理想境界。从这个角度看去,现代主义艺术体现着新的世纪精神,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秉承着传统经典理念的某些基本要素。
正如西方理论家西里尔·康诺利指出的那样,现代主义是从启蒙主义那里承袭了某些智慧质素的东西,如情绪化、内心化,乃至怀疑主义,以及从浪漫派那里得来的强烈激情与高度敏感。对技术文明推进的反感,有一种对自我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的明确意识等。为此,现代艺术变得更为极端,这是因为它们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危机,空前地感受到焦虑、抑郁、苦闷与彷徨,而沉重的忧虑感和迷惘心态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情绪,所以,现代主义的作品往往寄寓了艺术家自身对时代的悲剧性体验,他们的艺术表征着一种失去了现实归属及认同对象之后的某种放逐意味的美学意识。
以有限的材质去表现宏大的《超象》主题,我们的选择只能是精神性的,只能用直觉的方式展示出超越的幻想,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中把握内在的超越,其中的感情跌宕起伏,往往由个人出发,而联想到时空的广大而无穷。这是因为,面对着整体性的精神危机和巨大失望,我们期待着在“超象”的自由界面中重建精神家园,即一方面与物化世界进行抗争与努力,一方面又将自己的艺术探索深入到生命存在之中,而“超象”体现的是与之相对应的内心力量和精神价值,并将艺术思维的逻辑起点置于这个基础之上。
结语
艺术的伟大在于浑然苍茫元素的介入,因为它们包含着崇高之美的意识和成分,它们往往意蕴深长,总让人去追向和领悟超越生命空间的道理,并唤醒人对生命本质和事物本质的叩问,探寻其价值与意义的皈依,这也是我们重视并重提“超象”的意旨。这表明,艺术因此而卸去传统的某种重负,并回归到艺术自身,构成艺术作品的材质、形式语言的纯粹性与本色也因此被空前焕发出来。因此,“超象”的世界必然是整体的、神秘的,艺术中的“超象”在虚拟的视野中现身为神秘和无限。
在这里,整体是部分的整体,思考是无限的思考,于是,思考参与到无限之中,让形而上的波涛覆盖了一切。在作品《超象》中,元素的选择并未离开经验,表面看去,是可见的,仔细审视,不可见却无处不在,因而,它常常展示为浑然苍茫的诗意。画家不是哲学家、思想家,但他的特点是思考着“思考”本身,即他的思考就是答案,就是结果;我们从探讨“超象”出发,经历了创作的过程,最终又回到“超象”本身;在“超象”中,“感觉”是心灵的感觉,“发现”是发现本身,“寻找”是寻找本身,概括的说,它们都体现在瞬间的泼洒与滴溅中。“超象”是当代艺术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命题,“超象”的本质意义意味着,它不只是趋近天道的一种审美方式。
艺术方向论文投稿刊物:《上海艺术评论》创刊于1987年,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管,上海艺术研究所主办的以视觉艺术为中心、用图文并茂形式全面展示文化艺术风采的杂志。
SCI期刊目录
SCI论文
- 2024-04-24sci论文审稿结果一人拒稿一个接
- 2024-04-24Journal Of Zoology 杂志发文范
- 2024-04-24sci期刊投稿版权转让协议怎么弄
- 2024-04-22食品检测方向sci期刊选择方法
SSCI论文
- 2024-04-22ssci期刊分区怎么查
- 2024-04-18ssci论文更快接收的技巧
- 2024-03-27SSCI二区论文有什么快速发表的办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EI论文
- 2024-04-22土木方向国际会议发论文难吗
- 2024-04-17电气电力方向2024年的学术会议
- 2024-04-12EI会议发表文章的流程
- 2024-04-12真空、陶瓷、绝缘方面的会议怎么
SCOPUS
- 2024-04-15SCOPUS检索的会议怎么找
- 2024-03-23Scopus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属于什么
- 2024-03-14scopus论文着急见刊怎么弄
- 2023-12-25艺术教育论文可以发到scopus吗
翻译润色
- 2023-05-13神经生物学英文文章如何提升英语
- 2023-05-12sci论文润色的意思
- 2023-05-11生物医学sci论文润色有用吗
- 2023-05-09锻造相关中文文章怎么翻译为英文
期刊知识
- 2024-03-21论文发哪些期刊符合评高级职称要
- 2024-02-21论文发国际期刊的五大优势
- 2024-01-13英文、中文期刊傻傻分不清楚?这
- 2023-12-20地质比较好发的期刊
发表指导
- 2024-03-06哪些食品类期刊被ei收录
- 2024-02-29图书资料副研究馆员职称有学术专
- 2024-02-23准备评正高需要什么学术成果
- 2024-02-22论文发英文期刊原始数据包含什么